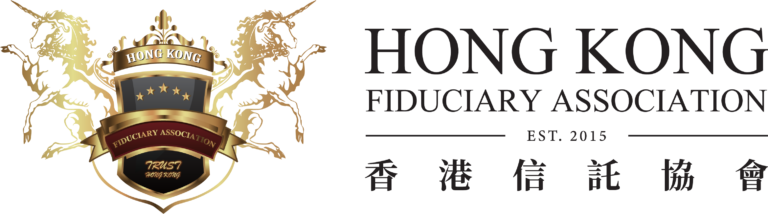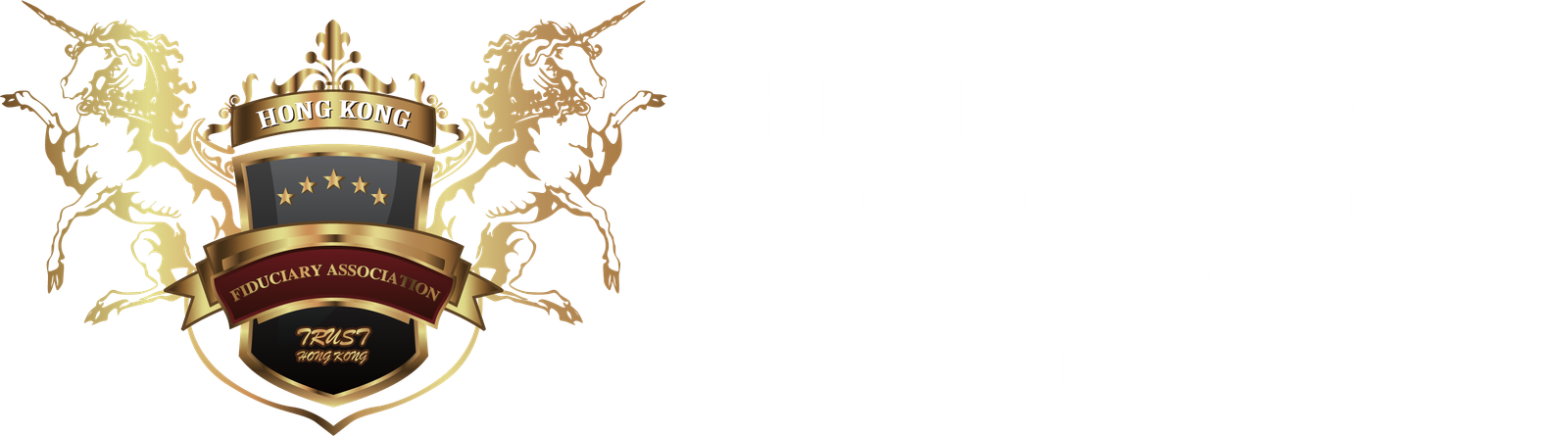迪拜基金會在財富規劃中的角色
迪拜正日益成為家族開展制度化財富規劃的重要樞紐。其中,迪拜基金會與DIFC基金會為資產整合、家族治理與傳承管理提供了成熟且公認的法律框架。透過運用此工具,創立人能有效實現所有權與控制權的分離,將資產納入基金會章程規範之下,從而清晰界定資產於生前與身故後的管理與傳承安排。
在實務操作中,阿聯酋的基金會廣泛應用於持有企業、房地產及其他區域性資產的家族架構。此類安排不僅在本地法律體系中具穩固合法性,亦獲阿聯酋監管機構與銀行普遍認可,成為關鍵本土治理工具。尤其在法定繼承制度可能導致財富轉移複雜化的環境下,基金會架構能顯著提升財富管理的確定性。對於希望透過迪拜基金會開展跨境規劃的家族而言,確保本土合法性始終是首要步驟。

迪拜與DIFC基金會的運作方式
迪拜及DIFC基金會均具備獨立法人地位,與創立人實現完全區隔。資產一旦轉入基金會,即由理事會依章程管理,不再由個人直接持有。此類架構不僅透過治理規則確保持續控制,亦能實現數十年的延續性。
基金會用途廣泛,包括家族治理、繼承規劃、公益事業及股權與不動產整合。憑藉高度靈活性與阿聯酋法律體系下的穩固認可,基金會正成為本地企業家與高淨值人士的首選工具。
與香港信託的相似之處
儘管基金會與信託源於不同法律傳統,但功能上有諸多相似。兩者皆能實現所有權與控制權的分離,確保資產依預設指令而非不確定繼承規則進行管理,同時可支援跨世代傳承規劃,透過制度化安排明確規定資產的分配方式與時間。
在治理層面,基金會章程與信託契約作用相近:前者可設定決策機制、爭議解決方式及受益人認定,後者則界定受託人權限與分配規則。兩種框架皆能突破個人壽命限制,為家族事務提供長期延續性與穩定性。
基金會與信託的關鍵差異
雖然信託與基金會有多項相似性,但在法律結構上仍存在本質差異。信託由創立人(設立人)將資產轉移給受託人,再由受託人以自身名義管理資產以惠及受益人;而基金會則作為獨立法人,直接以自身名義持有資產,並由理事會或董事會依章程管理。
此結構差異於實踐中具深遠影響。信託主要依賴一名或少數受託人行使管理職能,而基金會可由多位個人或機構組成理事會共同決策。這不僅影響治理效率與責任分配,亦對外部機構(如監管機關、銀行)的認可程度產生差異。
迪拜與DIFC基金會在跨境中的局限性
儘管基金會於阿聯酋境內具強效力,但其境外認可度並非始終穩固。部分外國法院、銀行及監管機構可能不承認阿聯酋基金會之法律地位。海外資產仍可能需經遺囑認證,或受當地強制繼承法約束,削弱基金會章程效力。
對於跨境資產配置廣泛的家族而言,這一現實突顯制度缺口。本土合法性雖穩固,但國際可執行性或受限。因此,以迪拜基金會為核心進行跨境規劃時,許多家族往往會疊加具更高國際認可度之架構,以確保全球範圍內的法律與稅務有效性。
國際家族的綜合規劃
在當前環境下,家族鮮少依賴單一工具。迪拜或DIFC基金會能於阿聯酋境內提供穩定性、治理架構與法律認可;而香港信託則憑中立地位與跨境可執行力,為全球資產提供保障。
因此,兩者並非替代關係,而是互補共存:基金會為本土資產建立治理平台,信託則強化國際資產的安全與傳承。此類整合式架構更契合全球財富格局,實現本土管控與跨境保護之平衡。

 简体中文
简体中文